无需单独注册,微信一键永登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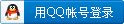
x
症状网络的小伙伴们近日与曾在媒体工作多年,现于澳洲从事社工的姐姐Wendy进行了一次对谈。Wendy主要从社工视角提出对诊断严谨性的思考,对用某些“标签化”的特征来判断疾病的犹疑。

Keywords: 疾病 标签化 诊断反思 压力 抑郁 应激 创伤 正常 价值取向
聊天对谈成员:
 精神诊断的标签
精神诊断的标签
Wendy
我的本科是传媒,硕士是社工,更多从社会角度看待双相与抑郁,在看到袁医生的文章之前,较少从心理或是生物的角度来看待精神疾病。社工的课程设置缺少精神病学基础,是一种缺口吧。因此,我有时会有怀疑疾病的诊断。精神健康领域的社工工作可能更多是帮助处理现实问题。 在澳洲,我们评估精神症状和它损坏经济来源的程度,来帮助患者获得相应补贴,帮助家人来解决照顾他们的难题,帮助他们寻找社群团体小组等,更多是社会角度的判别与援助。
Circle
其实听到您提到“社工,更多从社会角度看待双相与抑郁,较少从心理或是生物的角度来看待精神疾病”,我冒起了一种对精神医学自我批判的想法,即精神科医生趋向于认为疾病是生理的病变,药物的使用会忽略心理上的状况。 精神科的刻板印象常常被人理解为:强迫当事人来吃药以控制起来当事人,忽略忽略人的体验,社会、心理以及系统性因素。 其实更需要的的是专业之间的合作,谁也不占主导,大家是平等的。精神科医生调理生理;心理咨询师处理心理和行为因素;而社工处理社会因素。
Wendy
过于强调疾病的生物因素,会把人的情绪和行为都归因于精神病的诊断,认为它们是疾病带来的。我自己对于精神疾病的诊断是反对标签化的。而我与身边的一些有诊断的标签的个体相处时,我与他们相处时是去精神病化的。我并不喜欢正常这个词,我与这部分人相处的方式也不会有所不同,我更会关注什么让人有相应的症状,如低落沮丧。
Circle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在这里举一个反讽的例子: 有个人倾向于用发脾气、打人、砸东西来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因为ta从过去的经验中总是能够支持ta只要发脾气打人就能够成功的解决问题。假设ta并没有双相,但是ta因缘巧合得到了双相的诊断,此后会发生什么? ta下次再遇到问题,ta使用了发脾气打人,四周的人会怀疑ta没有好好吃药,把ta送到精神病院住院,同样这个问题,可能就用不同的方式解决了。 ta出院后,再次出现了需要用发脾气打人来解决的问题,ta又发脾气打人,这时,四周人只会觉得精神病人很缠人很难照顾,于是ta发现ta的问题没有办法被这个方式解决了。进一步,周围人会躲着ta这个“精神病”,觉得精神病人就是暴力伤人的,不愿意雇佣ta工作,不愿意和ta交朋友,逢年过节重要时刻居委会回来特别关心ta别惹事。
也可能会有另一种结局,就是ta发现ta再也没有办法解决,于是可能破罐破摔,稍有不满就随意骂人砸东西,完全放弃去克制自己的脾气,放弃去融入社会。
Wendy
疾病的标签,一旦赋予了某个人,会影响人看待自己、他人与社会看待自己。大多数的社会对于精神疾病还是有污名化的,还是多少会把精神疾病联想为反社会与攻击性的,把它与危险画上等号。 当一个人有这样的诊断标签后,周围人在对待他的时候就会更加谨慎,也可能因为人的不同而社交孤立ta。而澳洲的NDIS保险补贴与精神疾病是否长期终身相挂钩,如果被诊断为长期/终身的精神疾病,是可以领取到社会经济支持的。 因而,从社会/社工的角度来看,并不是反对诊断,而是持谨慎态度的。毕竟在外行人来看是一个黑箱子,交给精神科来判断。
Circle
说到精神科的诊断黑箱,常人往往觉得难以了解精神科的诊断。在精神科工作中可以遇到许多严重的、非常典型的精神疾病的发作,从业者常能见到明显不同于常人的症状,这一部分的人发病时候的状态,常人可能一辈子也不会遇到,或是顶多在街头巷尾稍微见到了那么几个令人回避的怪异的人。 在积累大量样本后,医生是会倚赖积累的经验来观察判断的。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好比预测某一些问题和特征时在复杂数据模型之中观察其中几个特征指标并以此预测的是这个人的不可控性。
Wendy
精神疾病污名化的标签其实还与阶层有关的,社会的价值取向。评判人的成就的部分,更使精神疾病患者,哪怕是稍有抑郁焦虑等情绪的人容易感到自己被审视,因而增大压力加重病情,诱发负面循环。社工工作中接触到不同的人,有一个来访有许多精神症状的诊断,她辍学工作生孩子,陪伴丈夫在军营…这些都是疾病这个点之外面的延展。
 双相与创伤
双相与创伤
Wendy
我最近也很好奇,我认识了一个人,他有双相的诊断。我在与他聊人生经历时,发现在他的疾病诊断外有许多的创伤,我就在想是否疾病的形成有创伤的影响? Circle
创伤会影响人的人格。也使人出现应激反应,形成相应应激方式。要区分的是出现应激反应后的应对方式还是疾病(如精神分裂、双相)本身所致的行为。比如近几年逐渐不使用的诊断,癔症。到底癔症是人的性格,还是创伤所诱发的应激方式?而照着诊断标准诊断后,观察异常是否能根据药物改善方才能来进一步判断病情。 再说双相,很多精神科医生会反对“创伤所致”,并更倾向于双相有是生理基础的、并不是纯外界诱因的。双相发病前是没有明显的异常的,药物压抑后也会恢复所谓正常功能;否则可能是人格的因素很多。
就算考虑性格问题,也不能放弃治疗

胡轩睿
分享自己的体验。曾经有一位医生认为觉得我的反应是夸张,他认为是我人格特质的问题而不是疾病本身。换了多个医生后才发现调整药物后我的病情是可调节好的。所以我想说自己的看法是希望多数人不要放弃调药。所以我认为医生也有自身的局限性。
Circle
也可以这样理解,没有办法把它赶走的时候别人觉得是你的一部分,而你是觉得双相的症状不是自身的一部分,用药物可以缓解好,让你回归你自己。
Wendy
抑郁情绪不是用意志力能克服的,也会使人觉得被责怪。很复杂的感受,一方面觉得如果我拿到诊断可以正当对他人说不要让我快乐起来,另一方面觉得有病理性羞耻感。会担忧标签会伴随我。自己是不正常的存在。当压力再大时会重陷进抑郁。 胡轩睿
在这里我想要补充一下我的故事,我是双相一型,从发病到治疗调整好,时间拖了两年,一开始看的那个医生也是调了很多药,调到后来,医生逐渐认为是我的人格因素,我当时也认为可能是我的人格因素了,反省自身的问题,但是还好当时并没有放弃调药。继续调整药物,现在吃了六种药,竟然就调好了,目前病情已经稳定了一年多。我这才发现,那些症状我一度以为是我的错,结果在它们消失后,我才明白这些症状并不是我人格的一部分,而是强加在我身上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与它们共存,也幸亏疾病的这个标签,让人们并不会误以为这些症状就是我。 Circle
一个时间段里与疾病共存过并不表示疾病就是他,他就是疾病。有些人的自我认同是抑郁症,有些是分裂样人格,等等。一个诊断并不能涵盖人的全部。过去的经历只是当时的他自己。但可以理解这样的感受,在正常健康的状态中时压力过激也会如此,有明显的抑郁发作,可能会担心它会再次来袭、影响认知功能等。当然也许特定的疾病(尤其是人格障碍)可能更需要治疗师自己有所经历才能治疗它们本身。
总结

徐水鬼
在我反刍阅读的工作中冒出了新的认知:很多时候精神疾病的定义[1]本身便是模糊、可随外界文化习俗的改变而变动的。因而诊断病人时的确要加入许多医生的主观经验与认知。它可能不像数学需普适性的良好定义、也不像哲学解构直达本质,在每一个精细的定义中探讨。因而下文的探讨必定也是在某种尺度上以片面“盖全”的(比如对谈中需要被定义的[正常])——正如疾病的“标签化”本身。所谓标签化的判断实际也是在短短几十分钟内评估病人状况的可行方式,而并非追溯到诊断学本身的方法论问题。因为技术与时间是有限的。确切来说技术的有限是指,如果脑科学、遗传学的理论发展到能够精准定位脑中的哪部分/哪些神经的异变和哪些基因确切导致了某精神心理问题的出现,且现有的仪器设施也足以让患者接受相关检查,那么可称技术是不受限、能最大程度严谨判断的。在不满足的情况下,选取所谓“标签化“特征来判断疾病就是一种有效方式。凝练后文Circle所说来看,即预测某一些问题和特征时在复杂数据模型之中观察其中几个特征指标并以此预测的是这个人的不可控性,使用药物后观察反应。因而我想“确诊的严谨”的概念是在一次次的医患交互、调节药物中建立起来的,而非单纯一次性辨别清晰后放之大吉。
这样便是对诊断严谨性的问题的一次解构。
同样的,下文提到的标签化,在确诊精神疾病可享受某种福利/保险的特定语境中,精神疾病的确诊在为人添上标签、使人从“正常群体”中异化出去的同时,换取来了社会对于个人公民责任要求的削弱和经济的补助、社会相应法律的宽松化对待。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将自我尊严让渡出去,得到一部分的庇护,便是异化本身的恶。问题是,社会如何在提供权益福利的同时,能够不让精神疾病患者的自我被让渡出去?反过来,相应法律宽松化对待这个群体是一种福祉的同时,如何不让某部分群体(如,真.有意识反社会)利用精神疾病的幌子开脱社会责任?这些依然是需要博弈平衡的问题。
而实际上解构精神疾病/患者群体的边缘化状态,便需解构不边缘/主流/正常的含义——福柯视角中的被规训——便会通向萨特所说他人即地狱[2]被看见即是被判断。如果其他人看着我,我会立刻被他们的注视修正与改变:我被注视,关乎我存在的要点。被注视是相关于他人的行为,是被冻结在不允许我自由行动的状态下。是他人使我们存在。人在他人的凝视镜映中存在,社会化的本质即异化,上述问题的根本也许是恒长无解的:不仅仅是精神疾病患者群体,任何带有特征的群体、社会性动物均是être jugé/regardé.
引[1] This is when a mental health problem is present, defined as: a problem experienced by a person which affects their emotions,thoughts or behaviour, which is out of keeping with their cultural beliefs andpersonality, and [which] is producing a negative effect on their lives or thelives of their families. This definition hides a very important factabout mental health problems, which is that they differ greatly in terms of their severity. ——Where there is no psychiatrist, VikramPatel
引[2]
Être vu, c’est aussi être jugé. Si autrui me regarde, je suis immédiatement modifié, altéré par son regard: je suis regardé, concerné au plus vif de mon être. Être regardé, c’est agir par rapport à l’autre, c’est être figé dans un état qui ne me laisse plus libre d'agir. L'Autre nous fait être. ——Satre,1964,commentaires sur Huis Clos.
 END
END编辑、排版、记录、写作│徐水鬼 编辑│Circle
排版│Aqu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