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需单独注册,微信一键永登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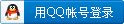
x
难忘的老物件·拉锯扯锯
春节期间探望一位老朋友,他是北京知青,下乡插队到内蒙的莫力达瓦旗,后来在加格达奇工作到退休,至今仍留在大兴安岭,只在春节期间回北京来住一段。就像兴安岭的劲松一样,他的根已经离不开大山了。前几年他曾去莫旗会友拍了一组照片,并写了不少睹物思旧的随笔。受其启发并征得他的同意,用这些照片,写些自己的感受。
时代进步,社会发展,好多东西总会渐渐退出人们的视野。不管是主动告别还是被动告别,当年的老物件总是寄托着我们的许多梦想与情感,今天看来更会令我们感慨万端。让过去启迪现在,让历史告诉未来,这些老物件即使失去了原有的功能,陈列在博物馆里也会述说着一段真实的历史……
“拉锯扯锯,姥姥家唱大戏,小妞妞也要去……” 这是一首遥远的儿歌。我们在农场时,拉锯扯锯的活儿可没少干。刚到32连,派给我的第一档活儿就是拉大锯。不过那种大锯不是截木头的而是破板子的,应该叫做顺锯或戗锯。只是拉这种锯需要一个高台,也就是锯架,戗锯架 。
我们是在良种连与领导矛盾到白热化后被作为“沙子”掺到32连的。我被分配给老刘头做搭档。老刘头出身富农,也是被监督改造的对象,他是木匠,话不多,出言十分谨慎。刚开始破木头时,连里没有电锯、带锯,就需要搭一个戗锯架。
锯架有一人多高,圆木打上墨线后通过跳板将它滚上锯架,就可以作业了。戗锯破板要两个人,一人站在锯架上,叫上锯;一个人在下面,叫下锯。这两个人的配合要默契,拉上锯的要用力将锯提起举过头顶,拉下锯的要配合往上推送;当拉下锯的用力往下拽时,拉上锯的则要顺势往下送。有一首类似劳动号子的顺口溜是这么形容拉戗锯的:“俩人分上下,对脸使劲弄,呼哧又带喘,就为一道缝。”
老刘头拉上锯,像个掌舵的,他要对准墨线,不能跑偏;我拉下锯,站在下面,一推一拽,反正那年头只要不惜力气,活儿就能干个差不离。就是有一点讨厌,因为要仰着脸,锯末子一个劲儿地往下掉,弄得满头满脸都是锯末子,碰到刮风更倒霉,眼睛里嘴里耳朵里脖领子里都是锯末子。
戗锯破板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节约板材,不像电锯、带锯破板,锯口宽,木材损失太大。那些珍贵的木料,如黄菠萝、核桃木,本来就不粗,再经电锯一秃噜,全变成锯末子了。
在32连学会使戗锯后,我后来在学校还与李振邦用戗锯破过黄菠萝木呢,不过因为木头细,不用戗锯架,只是将木头竖直绑在木桩上,两人都站在板凳上水平使劲运锯就可以了。
如今戗锯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听说伊春有个市民将半个世纪前使用的戗锯献给市文物管理站,还作为新闻予以报道了。
难忘的老物件·令人生畏柳罐斗
照片中的这个东东,问问年轻人能叫上名的恐怕不多。这是柳罐斗,汲水用的,作用相当于水桶,柳条编成,不漏水,也不易摔坏。咱们兵团不少连队用的虽然不是柳条编的,而是胶皮的,但也得叫柳罐斗,不能称之为“胶皮斗”。那时连队没有自来水,几百号的连队,人吃马喂,全靠水井。而柳罐斗、辘轳把就是汲水的必不可缺的东西。
兵团井深,深到吓人的地步。没有好身板,没有好膂力,很难从几十米的深井中摇上来一柳罐斗水。刚下乡时还都十六七岁,那些小女孩更是望井生畏。记得27连是军马连,专门负责打水烧水的是我们的校友,昵称“小波波”的杨松波,矮矮的身材,都挑不起来一担水。连里人多,连喝带用,一天要从井里摇七八十罐水,而马连的井似乎格外深,大概有六七十米深,一个小姑娘天天呼哧带喘的从深井里摇柳罐斗,那是多么繁重的劳动啊!尤其是冬天,北风刺骨,井台的冰哧溜滑,一不小心人就会滑倒,更甭说提着那么重的水桶了。那个情景现在想想都令人心惊胆战的,但小波波硬是完成了任务。只是她的手冻了多少回,肩膀上压得有多肿,半夜又哭醒多少回,只有她与几个好友知道了。
说柳罐斗让人生畏,还在于空柳罐往井里放的时候,不小心就会“咬”人。有的知青为了省劲,常常会玩“大撒把”,就是仅用手掌稍给点制动,听凭柳罐斗“自由落体”。如果躲避不及,胳膊、小臂就会被越落越快的柳罐斗带动的辘轳把击伤。不信可以做个调查,当年因为打水让辘轳把扫着的知青有多少?
如今农场家家户户都是自来水了,柳罐斗这玩意还真不好找了。
难忘的老物件·油桶烧柴难御寒
照片上的老物件是一个火盆,冬天用来取暖的。一般的火盆就用破脸盆代替或者是陶制的,这是一个铸铁的,可以说还是比较讲究、挺上档次的。
火盆要用炭,将烧红没了烟的火炭放在火盆里,端到屋子里取暖,因为是铸铁的,不怕踩,脚放在火盆边上烤也可以,只是要注意不要把鞋烤着了。
这个烤火盆,虽然不错,但还显得有些小家子气,是农村生产队用的。当年兵团烤火,一二百人的连队,几十号人一间大屋子,那得多少这样的火盆才能烤暖和啊!我们那时用的可比这个“气派”多了,论容积得有十个八个这个火盆吧——整个一大汽油桶一剖为二,俗称“半拉瓜”,扣在砖砌的底座上,炉门能塞进一个大树墩子,快赶上蒸汽火车的那个大炉门了。
记得有一年冬天去辰清独立营看望同学,他们的条件十分艰苦,没有青砖大瓦房,都住在帐篷里,虽说是棉帐篷,可四处透风。而且孤零零地搭建在树林里,夜里除了呼呼的北风就是野兽的嗥叫,让人毛骨悚然。帐篷里两排大通铺,中间地下一个“半拉瓜”,半米长的木柈子一块接一块地往里填,一会儿汽油桶就烧得通体发红。趁这个热火劲赶紧钻被窝。值班的战士夜里是不能睡的,他得不停地往炉子里塞柈子。一夜烧掉的木柈子可够吓人的。要说忏悔,这得算一条,滥砍乱伐,许多宝贵的木材资源就这样化为了灰烬!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心疼、可惜!
可就算这样烧,一停下来,帐篷里也立刻冷如冰窖。烧到后半夜,值班战士困得实在睁不开眼,也歪倒着睡去了。凌晨大家都冻醒了,炉子里早已火熄柴尽。你再看,好多人是戴着帽子睡的,帽子上都是一层霜。于是喊起值班的,再往炉子里填上柈子烧一会儿,才能从被窝里爬出来。
难忘的老物件·粉条漏子功劳大
北京台《非常记忆》中老孟提的“土豆熬(东北方言读nao)茄子,香死老爷子”,指的是东北的一道家常菜,黑龙江还有几道特色菜为人所津津乐道:小鸡炖蘑菇、猪肉炖粉条子。咱们在兵团时小鸡、猪肉不常有,蘑菇需要季节,倒是粉条子能经常见到,不过多是白水煮,少油寡味,不好吃。
粉条多见,是因为不少农业连队都有自己的粉坊,“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晴天的时候连里的空场上晾满了一排排的粉条,情形十分壮观。而做粉条离不了一个家伙什,就是图中的这个老物件,还有人认识吗?形似笊篱,但不是笊篱,这叫粉条漏子。
我没在粉坊干过,大致的制粉经过还是知道一些的:第一步是选料加工,将选取好的土豆洗净、粉碎、打浆、过滤、沉淀,就能得到淀粉了。然后开始和面,好像要加进去一些明矾什么的配料吧,和面是个重体力活,要和得不软不硬,硬了粉条漏不出来;软了粉条容易折,变成糊涂粥。接下来就该用得着粉漏子了,将面团放在粉漏子上使劲往下压,粉条就漏出来了,要漏到粉漏子下面的一口热水锅里,煮一下,再捞出来。这些说着简单,实际操作起来每道工序都有不少难度,和面的软硬,配料的精准,漏粉的均匀,水温的掌控,哪一道环节出了问题,粉条的质量也会受到影响。经过热水煮过的粉条要捞出来在冷水里浸凉,之后捞出来阴干、日晒,最后打捆。
作坊里用来漏粉的肯定要比图中的粉条漏子大,图中的漏子只适合小打小闹的。当年食堂的一些哥儿们还会将粉坊的残次品名为“粉耗子”的拿来做成美味,虽然没有肉与之同炖,但因为是小灶、油多,加上葱花、作料,“爆炒粉耗子”也是味美无比!
如今黑龙江的粉条形状也有了变化,不再是单一的圆形了,还有一指宽的宽粉,做宽粉图中的粉条漏子则无能为力,只有“下岗”了。而黑龙江的土豆粉条已经成为地方特色产品,因其比红薯粉、绿豆粉更劲道、口感好而更受欢迎,除了用来炖肉外,咱们耳熟能详的酸菜粉、炖四白(粉条、白菜、白肉、豆腐)、杀猪菜、得莫利炖鱼,粉条都是离不开的原料,在各地的饭馆里都特受欢迎。
难忘的老物件·大酱缸与泡菜坛
学校一体育老师是天津知青,退休返回家乡,听说我要参加“4.23”天津聚会,特地让我给他带两样东西:龙江酱膏与克东腐乳。毕竟在黑龙江四十年了,甜面酱与王致和竟然吃不惯了。
由此想到了兵团时老职工家中的大酱缸。那时连队的老职工家中,大酱缸是必备的物件,家家都要做酱,但奇怪的是大酱这东西,百家百味。那女主人干净利索的,做出的酱也透着一股香味;反之,女主人比较邋遢的,那酱的味道就差了不少。
我虽在农场过了两年小日子,但从没有自己做过酱,一是嫌做酱太麻烦——先要在头年秋季将黄豆炒熟磨碎做成“酱块子”,晾晒等其浑身长白毛发酵;然后等第二年春暖花开时将酱块子切碎按比例放盐放水,叫做下酱;三天后要用酱耙子(一根小木棍一端钉一个小方块)在酱缸里搅和,谓之打耙,早晚各一次,连打一个月。酱缸还要用纱布蒙好,风天不能进灰,雨天不能进水,不能掉蚊蝇,不能落杂物,如此娇气,伺候好这缸酱,比伺候孩子还难。二是妻子原籍广西,我原籍江苏,口味还是偏淡,一缸酱估计四五年也吃不完。所以想吃的时候随便找哪个老职工都可以要半碗,自己干脆就不做了。
我没有大酱缸,却有个泡菜坛,而且这个泡菜坛是自己改制的。泡菜坛的坛口比较特别,有一圈凹槽,那一圈凹洼处是用来盛水的,再扣个碗,坛内与空气就完全隔绝开来。那年想吃四川泡菜,又没有坛子,就从食堂要来一个空腐乳坛子,在坛口绑一圈细铁丝,然后编一个凹形的铁丝网,糊上水泥,抹匀,一个带凹形槽的泡菜坛就改造成功了。
泡菜原料是自家菜园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豇豆、莴笋、卷心菜、胡萝卜等洗净控干;烧开水晾凉,按照书上的介绍,加入少许白酒、红糖、盐、花椒、辣椒,一并倒入坛内,然后扣上碗,三五天时间就可以吃到酸酸脆脆的泡菜了。那味道不比现在超市买的韩国泡菜、四川泡菜差,更主要的是原料新鲜,绝对的环保、绿色。
难忘的老物件·热火朝天春播忙
“清明忙种麦,谷雨种大田”。在兵团农场,每年这会儿,麦场又该忙得不亦乐乎了。农业连队,麦场专门会配置一个排的“兵力”。其实不止春播忙,一年四季麦场活计不断,选种、拌种、制作颗粒肥,扬场、晒粮、作囤,最忙的时候还要常常全连大会战。当年种地有个“八字宪法”,叫做“水、肥、土、种、密、保、管、工”。这八个字,麦场涉及两个:颗粒肥、选种子。
扬场时实际也是对种子进行“初选”,人工扬场,那是一门技艺,手拿木锨顺风而立,向上奋力扬出木掀,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瘪子、草籽、都顺风“扬”远了,饱满的籽粒就在上风头落下。兵团后来有的电力扬场机,也要“借东风”,与人工扬场的原理相同。经初选留下的种子再进行“精选”就要用到选种机了。照片上是一个简单的木制选种机。一架木风车,就是一个木制的大风箱,一摇手柄,风箱内的叶片就转动继而产生风力,将较轻的杂物和瘪种吹出去,最近端流出的就是选好的种子。风车选种一般都在冬天,用手摇动风车手柄,要不停地摇,左手换右手,右手换左手,一人累了,再换一个接着摇,直摇得筋疲力尽,摇落太阳,摇落星辰。
我虽然不是麦场排的,但麦场的活儿也没少干。1970年春,我带着一帮小北京跟播种车,天不亮就下地,收工时已经晚上八九点钟了。后来才明白我们与机务是两种待遇,机务排开拖拉机是两班倒,我们跟播种车是一班到底不换人。站在播种机上,颠簸不算,那是真正的风尘仆仆,有条件的戴个风镜,没条件的就硬挺着喝风灌土,双手还要不停地在播种车里划拉,防止种子堵塞,还要注意流速均匀。到了地头,拖拉机掉头,我们则加麦种,加化肥,要扛着麻包小跑着去追播种机。
一天收工回来,正好碰见师首长来连队视察,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是农工排长。他看我的黄棉袄破旧不堪,腰间还扎着一条麻绳,除了眼仁有一点白色,牙都是黑的,整个儿一蓬头垢面,灰头土脸,所以十分不悦。后来与连长交换意见时竟批评我军纪不整:还兵团排长呢,简直像海伦跑过来的劳改犯!这批评传到我耳里时,师首长已经走了,我也只能苦笑笑而已。
难忘的老物件·即将失传的手艺
前年随天伦、老孔、高副回访团一行去农场,在32连见到了不少老职工,有李忠林、赵臣,还有铁匠吴廷富等等。提到铁匠师傅,不由得想起一门即将失传的手艺——挂马掌。
挂马掌,就是给马穿“铁鞋”,在马的四只蹄子上钉上铁掌,以保护马蹄子。据史书记载,挂马掌在公元前五世纪的游牧部落时就有了,到了唐宋时期,骑兵为了提高战斗力,防止马滑倒,都要给马挂铁掌。北大荒冬天冰天雪地,大道上溜光锃亮,马蹄容易打滑,必须挂掌。四个马掌算一套,马的四蹄都要钉,除非不干什么活的马。而农场的马干的都是重活:拉车、上山,跑远途,成天闲不着。磨损快的时候,十来天就得换一套马掌,最多二十几天,厚厚的铁块就磨成薄薄的一片了。32连有三挂马车,十几匹马,我那时跟何发师傅的马车,常看到马因为马掌磨损而影响脚力,这时就得去找铁匠了。
挂马掌要有特殊的“手术架”——如照片所示,是一个能容一匹马站立的架子。将马牵进去,拉住缰绳,使其不能乱踢乱刨,四个蹄子依次用绳吊起来,翻过蹄掌,置于备好的“手术台”上,把磨薄损坏的旧蹄掌撬去,拔除旧钉,用快刀剔去蹄上残余的老旧角质(这些边角废料用水泡发后可是浇花的好肥料),切削平整,再换上新马掌,用专用铁钉钉好。挂马掌是个手艺活,手艺精的挂得又快又好,马也不疼不闹。手艺糙的,钉子会打进马掌肉里,马一疼,就尥蹶子,干活走路一瘸一拐,更无法发力。当年农场都羡慕“听诊器、方向盘”,其实兽医、木匠、铁匠等也都是受人青睐的岗位,所谓“一招鲜,吃遍天”。在农村好的挂马掌师傅更能闻名遐迩,慕名想学手艺的也会趋之若鹜。
这些年来,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骡马牲畜渐渐失宠,而与牲畜伴生的这些行当也在走下坡路。据长春的《城市晚报》报道,白城子市已经把挂马掌列入该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正在积极想办法抢救这门即将失传的手艺。其实,正是因为稀缺,有些偏远地区着急挂马掌的还得跑上好远的路才能找到一处挂马掌的地方。不知吴师傅如今“尚能饭否”,如重燃炉火,也能为传承这门即将失传的手艺做点贡献!
难忘的老物件·地头窝棚故事多
听插队的朋友讲,农村不少地方有一句民谚:“丑妻近地家中宝”。说的是媳妇丑就没人惦记着,家里会太平;地近,上地干活就方便,路上所费的时间少,庄稼方便侍弄。
这两句话对兵团、农场来说并不适用,知青下乡,城里来的姑娘个个都如花似玉,丑妻反而很难寻;农场土地一马平川,一根垄就十来里地长。还记得32连四号地一根垄八里地,上午铲到头吃饭,下午铲回来收工。前两天看大个儿张建华写的《返乡记》,家家都上场部住楼了,离地块就更远了,有几十里远,都是开着汽车骑着摩托下地干活的。
因为家离地远,中午回不来,所以有时就会在田头地脑搭建一个临时休息的窝棚,有的简单点,如照片所示,四根柱子一个棚;有的则复杂点,为了避风还有拉合辫的泥墙。
咱们在兵团、农场时这种窝棚也有,不过不是用于铲地歇晌用的,一个连队上百人,不像农村单兵作战,小小的窝棚能容几个人?兵团的窝棚是用来看瓜的。那是许多连队都种过瓜,种瓜就要看瓜,怕夜里有人去偷,怕野兽去祸害,看瓜一般都是连队的老职工,不开面,较真,负责任。
刚下乡那一年上秋,营部附近种了块瓜,西瓜个头不大,比日本手雷大点,俗称地雷西瓜。三十连的笑林等人半夜拎着麻袋摸到瓜地,也不管生瓜熟瓜一顿扫荡,背回宿舍里大家狼吞虎咽可劲造,直撑得个个肚皮都像瓜了。尝着甜头后,第二天再去的时候出事了,笑林不知怎么踩着钉子,把脚扎了,一琢磨就是看瓜老张头干的,他把对付野兽的方法用上了,木板钉上钉子尖朝上扔在地里,不料没挡住野兽倒让笑林吃了苦头。振邦等一伙人来气了,拎着赶车的大鞭子跑到瓜地连抽几声炸响,向老张头示威,算是给笑林“报了仇”。
后来与老职工的关系处好了,看瓜的窝棚就又有一个用处了,就是男女知青绝好的恋爱场所。夜深人静,瓜地一隅,望着月色,闻着瓜香,听着虫鸣,卿卿我我,耳鬓厮磨,浪漫至极,温馨至极,好多朋友至今还能回忆起那种难忘的情景。
难忘的老物件·钐刀挥舞逞英豪
大个儿张建华在她的《返乡记》中介绍了不少农用机械巨无霸,令人赞叹不已。我们在兵团时虽然机械化程度已经很高了,但有时还需要辅以人工,比如虽然有了康拜因,但收麦子时还要用人工给康拜开道。要不这个庞然大物下不了地。而开麦趟子就要用一种特制的“洋刀”——俄式大钐刀。
钐刀形似镰刀却比镰刀大得多,用纯钢制成,半搾宽,四五十公分长,刀很薄,背有筋,从刀根到刀尖逐渐变窄。刀库镶嵌一根两米长的刀把,粗细有如锄把,与钐刀成九十度角。刀把上还有一个A字形的把手(右手握此处)。刀把下端至刀根处还有一个柳条弓子,便于将割下的麦子(或羊草)搂好顺溜摆放。
如果要评出当年三营“钐刀王”的话,当属27连一个老职工二毛子,只要给他备足了酒和馒头就行,茫茫麦海中只见他挺腰拔背,左肩一个行军水壶内装白酒,右肩一个书包装满白面馒头。手擎钐刀,抡圆一挥,一抱麦子就齐刷刷地躺倒在左手边,不一会儿工夫,足有三米宽的“胡同”就伸向麦海深处了。
我打钐刀,是到了三营学校后,几个男老师去给学校的老牛预备过冬的羊草。在一片大草甸上,五六个人一字排开,一个人开趟子,其余人渐次跟进,大伙儿把膀子抡圆了,从右到左,在草甸子画弧,“圆心”就是自己的双脚,“半径”是手臂加上钐刀把的长度,腰腹力量足的,半径会长点,割的幅宽也大一些。割下的羊草自然地在每人的左手边躺成一趟,晾晒一些时候再用钢叉将它们堆成草垛。等秋冬季时再用牛车拉回去垛好。
草甸子打羊草比麦海里开趟子技术含量要低一些,只要有力气就行。但因为草甸子没有麦田平整,有时刀尖还会碰到野蜂窝,这时就惨了,被惊扰的野蜂乱飞乱窜,这才真正体会到“一窝蜂”的含义。
累了,躺在刚打下的羊草上小憩,那叫一个惬意,望天空云卷云舒,闻身边香花香草,微风轻抚,不一会竟有人响起了鼾声。
钐刀不是磨的,而是砸的,将钐刀放在铁砧上(见照片),用小锤子在刀口上轻轻地砸(俗称“掂”),砸出鱼鳞状,再用油磨石扶一下刀锋即可。钐刀刀锋看虽凹凸不平,却是锋利无比,被钐刀扫到、割破,伤口很不容易封口。
因为钐刀,因为羊草,特别喜爱那种草甸上割草后的清香味。但在城市不容易闻到这种味儿了,只在割草机给草坪“剪头”时还偶尔能闻到。每到这时,就会想起在农场挥舞钐刀打羊草的情景,又见轻云舒卷,又闻芳草清香……
关于此号 旧事旧物旧情怀 念旧之人
|